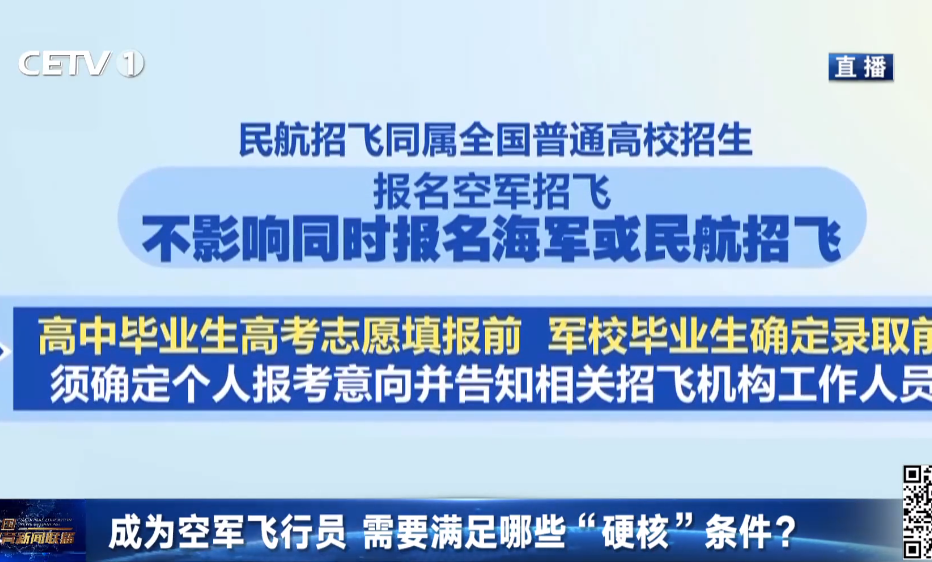夜读时光|一个“好欺负”的老师
发布时间:2025-05-20 22:00:29 来源:光明社教育家
怎样定位班主任?有经验的老教师告诉我:还是要成熟、严肃些,显得不好对付。我暗自窃喜,难道自己属于祖师爷赏饭的?因为我自认为比较符合这种形象。
首先,我体型比较彪悍,自然状态下的神情也不怒自威。其次,在正式成为公立小学教师之前,我有比较丰富的履历,较同龄人略显成熟。我在大学教过留学生学汉语,也在培训机构教过初高中生学英语;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便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公益活动,同时我的穷游足迹遍及全国。除此之外,我还比较喜欢动笔记录教育思考,陆续发表和出版过一些文章和作品。
通过以上介绍,大家也许会断言:这应该是一位不好惹的老师!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但在我教过的调皮学生眼中,我却是一个“好欺负”的老师。
男生小松,就是我教过的调皮捣蛋学生之一,也是说我好欺负的那个人。
小松爱动手,总是主动出击、屡败屡战。而且每次都以同样的仪式结束战斗:整个身体在滚动中与地面亲密接触,并时不时地伴随着与大地撕心裂肺的“虔诚对话”。每每这时,我都会把他叫到安静的角落,让他把起因经过说出来。我不批评他,也不急于责令他认错或道歉,顶多追问几句“然后呢?”“那你呢?”“为什么呢?”。
有时我太忙,就让他先把事情经过画一下,因为好多字他还不会写,画下来再讲的时候能节约不少时间。时间久了,他爱动手的“毛病”虽然没有完全改掉,但先动手的情况少了,也不是总需要靠“拥抱大地”抚平内心了。最重要的是,小松从爱动手变成了爱动笔。
在我的鼓励下,小松阅读了大量绘本,并经常用绘本的方式记录生活。我还帮他联系了某杂志的编辑,发表了他创编的故事配画。“放荡不羁爱自由”的他,比别的孩子学会握笔、写字要晚一些。辨认他的字,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但经过我不断的指导和他断断续续的努力,终于在三年级的上学期,他的字均匀了、清晰了!一天下午,他用所有人都能清晰辨认的、空前清秀的字样,在楼道的外墙上竖着写了几个字:大吴老师死了。那是一个期末。上午的英语考试快结束时,他先是以捡橡皮为由离开座位,后来又给同学传纸条。我因此收了他的卷子,他就给我写了“大字”。
那些字不是我发现的,是我“粉丝团”的一个女生看到后冲进教室大声宣布的。瞬间,耻辱感和挫败感将我包裹。我好难过,他根本还是那个小野兽,现在喂大了,狠咬我一口。我强忍着愤怒对全班说:“希望写字的孩子私下主动来找我。”我偷偷瞄了他一眼,愤恨中又生出本能的怜悯:“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也不好受。”
我等啊等,却音信全无,与等待一同坠入海底的还有我对他的期待。转眼到了第二学期,开学那天,我的桌子上突然出现了一瓶熬好的梨汁,我知道是他悄悄来过了。把瓶子还给他时,他跟我聊了很多。其实那天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不过,这件事后来被他不厌其烦地套进不同题目的作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当时,我……》《我的老师》《有你, 真好》。
他在作文里写道:“大吴老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之一。”我又一次被他“骗”到幸福得晕了头。我总这样,被学生“骗”——不,我总是这样:把解决不了的交给时间,把想要成就的交给笔。很多年后,再聊天时,小松说:“那件事,是我俩关系的转折。”“说实话,在那之前,我多少有点觉得您好欺负。我犯了错,您总是让我说一说发生了什么,不会写的画也行,还允许我为自己辩护,除了承担自己的责任,也不用跟您道歉,反正无论怎样您都会选择包容我,相信我能变好。”
“为什么那件事是转折?我变得不好欺负了?”
“不是,大吴老师,您没变。是我变了,我不想再让您伤心了。”
小学毕业很久后的一天,小松发信息说自己的摄影技术有长进,要给我和家人拍一组照片。拍照那天,小松开玩笑地问我,班里还有没有学生“欺负”我?已经长成一米八大个子的他说要去帮我震慑他们。我得意地笑道:“不用你去震慑,我有法宝。那些调皮的娃娃都跟你一样,通过写作找到和看到了自己。”
但我还是会把“好欺负”的教师人设延续。允许调皮的孩子犯错,耐心地陪着他们用写作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并坚定地鼓励和支持他们,追寻心中更好的自己。


 投稿
投稿 APP下载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