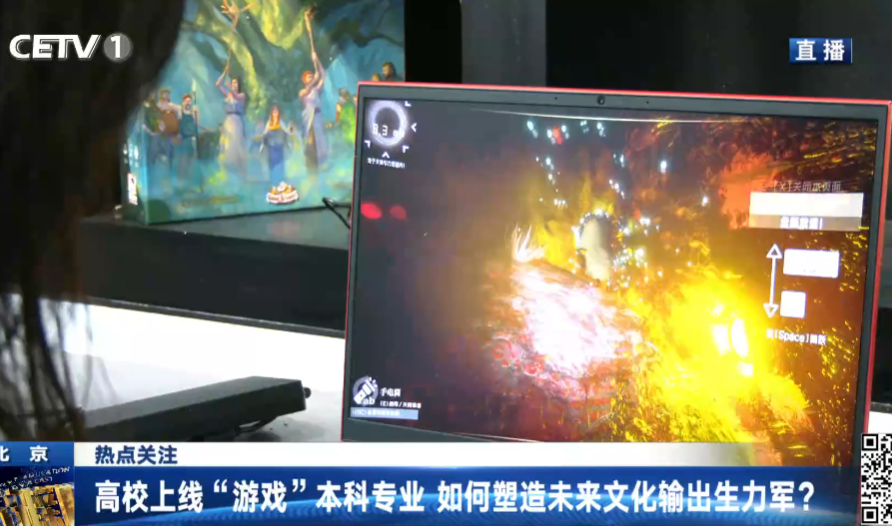好大学的模样
作者:游宇明
发布时间:2021-09-03 15:53:06 来源:教师报
易中天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厦门大学的野蛮生长》,其中有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就是:“何谓大学,非大厦也,亦非大师也,乃大度也。”
易中天这句话充满了人生感慨。高中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当兵团战士,后来在乌鲁木齐钢铁厂做高中语文老师,1981年考上武汉某著名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课教得特别好,课堂上场场都是座无虚席。然而,欣赏他才华的老校长退休后,他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同事们能分到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他只能拥有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后辈们一个个评上了副教授、教授,易中天却长期顶着个讲师的名头,有段时间甚至被取消授课权,直至1991年才评上副教授,这还是“提调”,即你要走了才给你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92年,易中天毅然离开了武汉。
来到厦门大学后,易中天发现:天空还是那个天空,“人间”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他刚调来的时候,专业不对口,只能在艺术教育学院教点艺术概论,课时不够,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郑学檬便“夺走”艺术教育学院院长兼任的艺术研究所所长帽子,按到易中天头上,并且交代:想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学校不干预。这种大度让易中天特别感动。很快,易中天便用学术成果回报,三年后,他的《艺术人类学》获得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的成果共14项,其余13项的得主都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只有易中天是副教授。林祖赓校长和郑学檬副校长觉得必须给易中天评个正高,艺术学院没有指标,便动用学校公共名额。
获了奖、评上正高之后,易中天在社会上有了较大的名望,常常会做各种学术奖项的评委,有次省里评奖,他还是召集人。兄弟院校派出的评委都是带着任务来的,谁都希望给自己的学校多争取些奖项。厦门大学自然也有这种想法。可易中天做评委完全是“吃里爬外”,他定了这么几条规矩: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兄弟院校优先,职称低的优先,从未获过奖的优先。这样“三个优先”活活将厦大给“出卖”了。可是厦门大学生气了吗?没有。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陈传鸿和统战部长官鸣向省政协提名,说这人可以去做委员。
大度对一所大学的意义非同小可。大度会使人包容。学术研究的真谛莫过于从事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事情,如果校方老是给学者出题目、定方向,也可能弄出些所谓“成果”,但成果的质量一定会打折扣。大度也会使人公正。一个团体、一级组织要求成员看重整体利益,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个人确实显出了出类拔萃的能力,我们就要给他适当的位置,这样,一则可以更好地激发他本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其他人建立榜样。大度还会使人看淡小圈子的得失。人也好,组织也罢,有得失之心可以理解,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将小圈子的利益置于大圈子之上,也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只服从局部利益,否则,大学就难有格局,也难以涌现像易中天这样被社会公认的大才。
易中天在文章中有段话说得特别好:“大学有如大地,不能要求都是人工栽培,总会有些植物野蛮生长。唯其如此,才千姿百态,欣欣向荣。”以此观之,厦门大学堪称当下好大学的一种样板。


 投稿
投稿 APP下载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