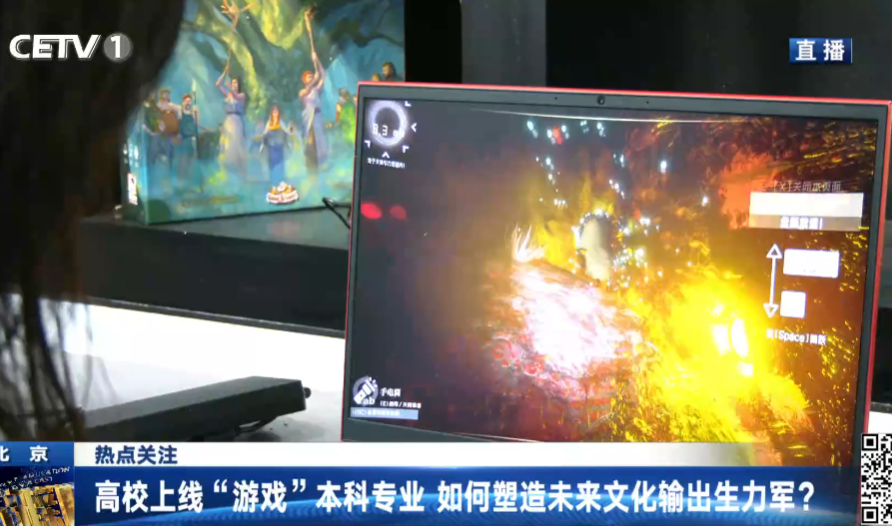一曲花间万古传
作者:贺拴运
发布时间:2020-10-29 09:22:50 来源:教师报
余与《花间集》,颇有渊源:少时从先父习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即识得花间一派;嗣后求学汉中,曾购得盗版《花间集》,印制粗劣,颇碍眼目;再后执教尧中,探秘图书馆古籍室,偶得清刻本《花间集》,刻印精良,字迹清晰,实为影印之佳底本,遂生影印之意。
庚子春,瘟疫肆虐,举国隔离,开学无期。正月中,与王艳丽诸同志参与网课,间隙影印《花间集》。先扫描,次修图,再制版。至庚辰己丑,版成,以宣纸一比一比例印之。
校藏清刻《花间集》,十卷一册,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版心题书名,鱼尾下记卷次、页码;半叶十行,行大字十七。书宽十四点八厘米,高二十六点一厘米。卷末标示“京都琉璃厂炳文斋李刻”,卷尾有清光绪十九年(1893)王鹏运跋。
《花间集》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收录晚唐五代词家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家词作五百首。在敦煌曲子词被发现之前,稳居中国最早词选第一近千年。遗憾的是,关于编选者赵崇祚,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流传。《花间集·序》中涉及赵崇祚生平,仅“卫尉少卿字弘基”七字。作为唯一编者,赵崇祚也没有在《花间集》中留下只言片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怀疑他是中书令赵廷隐之子,也只是推测,没有实证。虽然,历史还是记住了赵崇祚。千年后回首,究竟是赵崇祚成就了《花间集》,还是《花间集》成就了赵崇祚?怕已很难说清。
《水浒传》开篇引邵尧夫诗说:“纷纷五代乱离间。”在这样的乱世中,赵崇祚竟然做起了文化工程,实是难得。掩卷沉思:如果没有《花间集》,这五百首词作能否流传下来?
当然,这或也与当时蜀地的特殊情况有关。黄巢起义,北方大乱,五代迭更,诸侯国你方唱罢我登台,而蜀地依赖“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天堑得以苟安。《花间集·序》说:“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于是,你歌我舞,曲子词大盛。花间十八家,就有十五位活跃于蜀:或生于蜀,或宦旅于蜀。蜀地词坛风光无限。
《诗经》上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看见灿烂的桃花,联想到美丽的新嫁娘。可见,数千年前,国人即以花喻美人。李白《长相思》直说“美人如花隔云端”。《花间集》五百首,主角是谁?是《诗经》和李白的“花”,于是,取名《花间集》。《花间集》词作,写不尽美人情态、闺怨爱恨,历来被称为艳情之作,为人诟病。其实,和平年代,有此之作,实属正常。毛泽东说文艺要“百花齐放”,《花间集》也是一花。
《花间集》用词华丽,作者是下了工夫的,且不乏名作。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韦庄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历来为世传颂。论题材,《花间集》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艳体,亦有表现民俗的,如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等,虽少,但也格调明快,别有风味。
《花间集》五百首,皆是短小精悍的小令,这与宋词不同。宋词有小令,也有长达百余字的长调。小令也好,长调也罢,各有特色。但就阅读体验,个人还是喜欢小令,易诵、易记、易理解。说到底,词也是歌。一首歌,若唱了三天三夜还没唱完,你能接受到多大程度?
《花间集》无长调,或与所处时代有关。词起于中唐,长于五代,盛于两宋。《花间集》词人活跃时,长调尚未出现;结集时,距陈桥兵变也有二十年。无论如何,《花间集》将汉语言简意赅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如写相思:“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说,词问世后,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广深(广而且深),一是狭深(深而不广)。《花间集》走的是狭深之路。这条路不好走,题材狭窄,束手束脚。人生百年,世事百态,谁人能天天卿卿我我?终于,宋词来了,世间万象皆入词,《花间集》偃旗息鼓,黯然落幕。
遥想当年,《花间集》初问世,定然洛阳纸贵,千余年后,泯然故纸堆矣。今日读《花间集》,推崇不必过甚,贬抑不必过头。以平常心看之,不过千年前之歌曲集罢了。
一代有一代的使命。《花间集》的时代早已风流云散。


 投稿
投稿 APP下载
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