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的回忆
作者:刘朱梁 赵爱民 肖 铁
发布时间:2024-09-26 15:12:04 来源:陕西教育·综合
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以下简称“干小”),1944年夏开始筹备,地址在延安东关飞机场北面、二五九旅家属队东邻的一个小山沟的一个扇面的坪内,就岩面挖了两排人字形的窑洞,有二十几孔,此处原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旧址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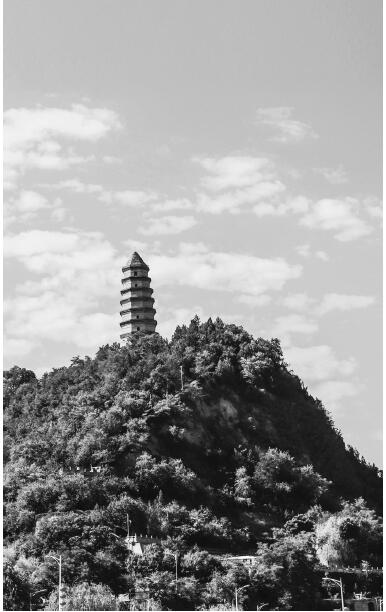
1944年8月,朱梁同志(现名刘朱梁)由西北党校调延属干小任教导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1944年底,傅崇杰同志任校长,三四个月后他被调去边区教育厅工作,专署又调王成舟同志接任校长工作,一直到1946年秋,干小与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第二小学校(以下简称“二保小”)合并。1946年4月,因地下工作需要,朱梁同志被调去中央党校学习,后跑地下交通。教导主任由曹运昌同志接任。
(一)
当时干小的生源主要是驻延安的中央、地方机关的干部子弟及延属各县县级以上干部的孩子。大约有300名左右学生,三四十位教职工。学校采用边区教育厅统一编印的国语、算术课本。刚开始只有幼稚班有保育员,后来逐渐给小学低年级也安排了保育员。
学校有自己的农场,可以自给供应蔬菜和部分粮食。在总务同志们的努力下,伙食相当不错,有一段时间,每人早上都能吃上一碗牛油茶。
当时学校执行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二年级学生就可写出通顺的家信,三四年级的同学可以写出有一定思想内容、语句通顺的日记、作文。辛安亭同志编辑出版的边区《儿童作文》《儿童日记》中有不少是干小三四年级的学生写的。肖铁同志回忆,他当时刚从农村来,一字不识,到二年级的时候,便能给家里写信,母亲对此事既惊奇又高兴。学校对文化课也很重视,并且注意学用结合,教学效果也比较好。
有革命的教员,才能教出革命的学生。学生们的健康成长,与具有革命理想又朝气蓬勃的老师、阿姨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学校始终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傅崇杰、王成舟、朱梁等同志都是鲁迅师范学校的学生。鲁师的校歌《救救孩子的呼声响在二十年前》“用健康的乳汁哺育孩子们,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经常响在他们耳边。他们以及其他教师通过高年级的“公民课”、低年级的“故事课”,给同学们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思想。曾经有一次测验,是问同学们长大想干什么,多数同学回答:当工人做枪炮;当农民种粮食;当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也有回答当科学家、工程师的。有一次王震将军来校视察,问一个男孩子长大后要干什么,孩子大声回答:“跟王旅长当兵!”逗得大家都笑了。故事课是对低年级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很好的形式。有同学回忆到,朱教员(即朱梁)讲的荷兰儿童故事《爸死了》,使他们接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一只胳膊的孩子》教育他们要做宁死不屈的小战士;刘珍卿老师讲的《白雪公主》教会他们分辨善恶是非。
(二)
在学校,从来没见过王成舟校长愁眉苦脸,也没见过他发脾气,他总是笑眯眯的。遇到同学打架,他还是会笑着,轻轻捻住打人者的耳朵,拉到一旁轻声细语地讲打人是不对的。他亲自给学生带课,有的同学至今还记得王校长给他们上故事课,讲述了《袁副总司令的弟弟》《王震将军的警卫员》《王旅长与炊事员》等故事。有同学说他们只见过王校长流过一次泪:1946年4月,一天的晨操结束后,他得知“四八”烈士遇难的沉痛消息后哭了,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朱梁老师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充满革命热情,敢想敢干,他自己动手写校牌,用锡制校徽,“延属干小”四个字涂上红漆煞是好看,他提出在同学中组织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并领着一二年级的同学到飞机场挖苦菜,讲防旱备荒的道理,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在大生产运动中,他是劳动能手,纺线质量被评为头等。傅崇杰同志离校以后,有一次回校看孩子们,被他们团团围住,说长道短,简直脱不开身。当时那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难以用语言形容,现在想起来,依旧令人十分神往。正如雪原老师教同学们唱的干小校歌的歌词“延属干小是我们的家,校长(老师)是我们的妈妈……”(赵爱民同学回忆)。何恒老师带“唱游课”时又唱又跳,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的神情,刘治华老师循循善诱的慈祥面容,像木刻画一样印在同学们的脑海里。还有曹阿姨(曹宏同学的母亲)领我们到延河洗澡,晚上叫小同学起夜撒尿,她对同学,特别是对调皮的同学会比较严厉一点,但她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炊事班的王世福叔叔,每天不停地到延河驮水,供全校同学吃、喝、洗、用,不见他多说话,总是笑嘻嘻地埋头干自己的工作。与二保小合并、转移的路上,他管收容队,吆一头黄牛,驮着同学们的行李,并让掉队的同学刘联、刘盈等跟着他慢慢赶路。在这个革命家庭里,每个教职员工都为培养革命的后代竭尽自己的全部心血。
由朱梁老师提出,经学校研究决定,在高年级同学中成立“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在低年级同学中成立“新民主主义儿童团”,这是1945年后半年的事情。肖铁回忆,他当时是低年级学生,级任教员是刘治华老师,曹教员宣布的儿童团名单中有他们班的施玉英、钟灵、何荣芳、杨旺(杨常新)等同学,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曹教员宣布完说,名单上没有的同学要继续好好学习,努力争取以后加入。散会后他心中老大不髙兴,也没心思去玩,一个人回到教室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翻书。刘教员注意到这个情况,轻轻走进教室说:“第一批儿童团员里有你,给教导处报过的,是念漏了,去参加选举团长吧!”他这才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儿童团的团长选举活动。选举的结果,儿童团长是大个子女生施玉英,“我们之后便在她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当时‘铁木尔活动’在同学中产生的影响很大。我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听曹教员讲‘铁木尔及其伙伴’的故事,听朱教员讲‘落花生精神’。铁木尔的故事,解放后有相关的书出版,人们比较熟悉,‘落花生精神’却少有人再谈起。‘落花生精神’是毛主席讲话中的一个比喻,说我们应该学习落花生,它生在沙土里,长得又白又胖,人们看不到它,它也不出风头,收获后炒了很好吃,为人类谋利益。我们应该像落花生一样,不为名、不为利,埋头苦干,做了好事也不被人民所关注。听完故事后,少先队和儿童团很快开展了做好事的‘秘密活动’。”肖铁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团长秘密布置他们第二天早晨扫校院,晚上他们就偷偷把扫帚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天还未亮,团长就在窗外打个暗号,他们一个叫一个悄悄地起来,开始行动。先从自己宿舍门口扫起,只听见扫帚“刷刷”响,大家工作得很紧张。偌大个院子,眼看就要扫完了,起床铃却突然响起。为了不泄漏“秘密”,他们提着扫帚就往宿舍跑,迅速钻回被窝假装睡觉,这时宿舍内的其他同学眼睛还没睁开。后来学校里经常出现不知名的好人好事,但只有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心里明白是什么情况。
生产劳动是当时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活动之一,各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班级的地,栽西红柿、种水萝卜。很多同学是农村来的,只要给他们些微指导,劳动成绩就很好。夏天睡午觉起来,一人就能分到一个西红柿或水萝卜吃。学校在山坡上种了大片的洋芋、苞谷等作物,到了收获的季节,学生会劳动委员王必雄的哨子一吹,大小同学拿上工具就跑。挖出的洋芋,筐子、口袋装不完,有的同学就把裤子脱下来,裤口一扎,能额外装不少。上山劳动还有件趣事,就是能利用劳动的休息时间挖不少小蒜,拿回来洗净、切碎,放在茶缸里撒一把盐,就着饭吃,味道可真美!除了这些劳动外,为了防旱备荒,中高年级还有挖野菜(类似现在的小秋收)的任务,凡是能吃的像苦菜、蒲公英叶子等都挖回来,然后过秤登记,晒干储藏,以备在困难的时候和在饭里吃。
(三)
为了配合学校的教育,学校还和家长联系,希望家长告知学生在家的表现,以便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更强的教育,也希望家长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对孩子开展更切合实际的教育。朱梁老师回忆说,这种措施在当时的效果很不错。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孩子在学校从不搞特殊,同学们都不知道他是谁的孩子,大家都是一样的,在一起愉快地学习、劳动、玩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记得当时有个叫马汉臣的小同学,其父亲好像在三五九旅搞后勤工作,家中对马同学十分娇惯,缝了一套像美国驾驶员穿的麻色(蓝中带白色)制服,配上船形帽,穿戴起来很神气,这孩子最爱在同学中吹嘘他爸爸的“官”如何如何大。老师针对这种情况讲了“斯大林和他的儿子的故事”,说斯大林的儿子上学念书时,从来不给同学讲他是斯大林的儿子,因为父亲是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同学们应该好好学习这种品德。这个故事对同学们的影响很大,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夸耀自己家长的职务了,即使解放后大学毕业了,同学们都鲜少知道其他人的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
学校也会及时组织同学们参加一些校外的社会活动,这对学生的知识增长、思想成长很有益处。有些同学至今还记得到陕北著名民间艺人韩起祥说书中“刘善本,心本善,驾上飞机到延安”等书词。全体师生在东关和群众一起夹道欢迎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中原突围凯旋,王震旅长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英雄部队英姿勃勃的气概,叫人看了十分感动、振奋;欢送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孩子和大人们一样悬着一颗心,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欢迎毛主席从重庆胜利归来,孩子们活蹦乱跳,说不尽的高兴;延安各界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四八烈士”追悼会时,干小的孩子坐在主席台下和大人一起悼念遇难的革命英烈王若飞、邓发、秦博古、叶挺。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懂得了革命的曲折艰难。追悼会之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继承先烈们的革命遗志。
当时,学校的文娱活动十分活跃。在这方面,曹庆让、雪原、何恒、王国英诸位老师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组织的晚会上,排演过边区流行的秧歌剧《小姑贤》《兄妹开荒》《好庄稼》和曹庆让老师编导的《毛主席去重庆》。这些活动既活跃了当时的生活,又让同学们受到了教育。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阳历年给毛主席拜年,在王家坪窑洞前的院子里,延属干小的秧歌队扭完了镰刀斧头领头的大秧歌舞,便开始表演节目,其中“毛主席去重庆”是最受欢迎的。毛主席抱着自己的女儿,围条大围巾,穿着灰棉衣,笑眯眯地和观众站在一起,很认真地观看孩子们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央机关同志拿出红枣、花生请同学们吃。这时谁还顾得上吃东西,大家都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握过一次还排回队尾想要再握第二次。记得李鼎铭先生的孙女李彩云,抢着和毛主席握过两次手,回校以后一再向没去的同学讲述,分享她的幸福。从这次的拜年活动中,大家受到了生动的教育,感受到了党的温暖,看到了党的领袖和群众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这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对这所革命小学校,党和政府非常关心,不少同志常来校看望。王四海是干小一年级的学生,王震将军作为其家长,曾数次来校与校长、老师交谈,平易近人,并给予学校很大的支持。老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遇难前也曾拄着拐杖来校视察,王校长陪着黄老先生到学生宿舍、教室看看,指着孩子、教员给他介绍,老先生捋着胡子,微笑着,不时地点头赞许,认为在边区经济条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在简陋的窑洞里,把教育工作搞得如此出色非常了不起。
是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延属干小的同学,无论是疏散回农村的还是在行军途中并入保小的,在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表现都是不错的。有一个叫张林香的女同学在疏散回延川的路上被敌人抓住,强迫她带路,她竟然毫无惧色,从容不迫地将敌人带入我军的伏击圈。当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时候,她却机灵地摆脱敌人跑了出来。这个故事在后来的保小,是人人皆知的,惠怀国老师还把故事写进书里。解放后,在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读过书的同学,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中不少同学在党政机关担任要职,在文教、科技、工业、经济等各条战线上成为专家学者。
延属干小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所革命摇篮中的生活,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所接受的教育。延属干小的学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培养。
作者:刘朱梁,笔名梅笑,兰州军区离休老红军,著名书法家。赵爱民,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教授。肖铁,兰州炼油石化总厂退休干部,高级工程师。

 热点新闻
热点新闻
 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

 投稿
投稿 APP下载
APP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