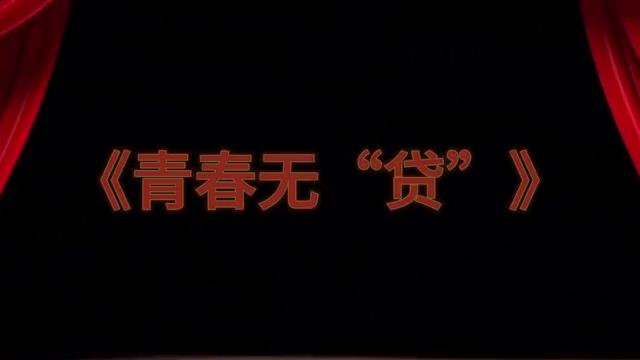身体哲学视域下体育教育的价值反思
发布时间:2018-01-19 15:16:29
从词源学的角度,在我国古文献里主要从“身、体、形、躯”来定位身体教育。“君子之学也……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美七尺之躯……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身体教育是通过教化、修养来达到对君子之身的塑造,改变身体外在的形态结构,这种教育过程是按照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来加以规制和形塑,由此形成的身体观不仅存在于身体本位的物质空间,还与社会空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1]。西方身体教育最早源自古希腊身体术语,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把身体看成是“器官”“有机体”,身体的肉体骨架被囚禁在精神世界的牢笼之中,形成与精神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教育本身隶属社会范畴,对身体的教育自然也就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把“身心二分”聚焦到心智层次,采用“非具身性”(disembodied)[2]思维来表现身体的双重思路,身体本身表现出“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t)价值样态。霍布斯和福柯从社会建构的视角试图揭开身体教育的话语规则,身体作为社会教育的定位场所而存在,但尚未挖掘身体客观存在的生命态、情感态的价值取向,生命态身体的本位回归是社会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元素。可是,按照这种社会思维来构建的身体教育实质倾向于社会意识、社会发展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身体教育的缺场。

 热点新闻
热点新闻
 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

 投稿
投稿 APP下载
APP下载